老子·第五十五章——含「德」之厚,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,猛獸不據,玃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。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,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嗄,和之至也。知和曰「常」,知常曰「明」。益生曰祥。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,謂之不道,不道早已。
分析:含容道德深厚的人,得到道的呵護,與嬰兒得到母親的呵護一樣。對於嬰兒,有毒之蟲類不來蜇害,兇猛的野獸不來撲捉,善抓善捕的鷹鳥不來攻擊。他們筋骨柔弱卻能把東西牢固地握住,不知道兩性交合但是生殖器官卻能自然興奮起來,因為他們精氣純正。他們整天哭號卻不會嗓音沙啞,因為他們與自然的呼吸一樣和諧。
知曉自然的和諧之氣,也就理解了永恆不變之道。人們知道了永恆不變之道,就有可能達到明察的境界。但是,人們卻想要增加自己的生機,認為這是可以達到長生目的的;然後,人們又根據自己的心愿而役使精氣,認為這樣可以變得更強大。
看起來,從嬰兒到成人,似乎是越來越強大了,但是,萬事萬物都是一旦強壯了就開始衰老了,追求強壯是不符合大道的,不符合大道就會提前導致死亡。也就是說,失去了自然之道而追求強壯,反而會加速死亡,不如復歸於嬰兒。
老子·第五十六章——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。塞其兌,閉其門,挫其銳,解其紛,和其光,同其塵,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,不可得而疏,不可得而利,不可得而害,不可得而貴,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分析:真正了解大道的人不去多加解說,一定要把大道解說清楚的人不是真正知道大道的人。因為大道是無法用語言文字解說清楚的。堵塞自己的口耳,關閉自己的眼鼻,不去受道聽途說的干擾;解除自己的稜角,排除紛雜的頭緒,讓自己的心靈與自然之光相和諧,與大地塵土同在,也就是說物我合一而不強調自我的存在,這可以叫做與玄妙的的天道同一。能夠與天道同一,那麼,也就不必再求親近,不必在乎疏遠;談不上對自己是否有利,也談不上對自己是否有害;不必把什麼看作是尊貴的,也不必把什麼看作是卑賤的,這樣才能成為天下真正最為尊貴的。
老子·第五十七章——以正治國,以奇用兵,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?以此:天下多忌諱,而民彌貧;人多利器,國家滋昏;人多伎巧,奇物滋起;法令滋彰,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:「我無為,而民自化;我好靜,而民自正;我無事,而民自富;我無欲,而民自朴。」
分析:治理國家要用正道,用兵打仗要用奇變,治理天下要不有意做什麼事。也就是要掌握正變與無為之道。我什麼知道應該如此呢?根據我今日所見的情況。現在的天下充滿着忌諱,有太多的教條,但是百姓卻更加貧窮;百姓有太多的權謀計較,國家政治卻更加昏暗;人們有太多的技能智巧,離奇古怪的東西卻越來越多;法律命令越來越清楚,盜賊卻照樣非常眾多。所以,聖人說:我不憑個人私心去做事,但百姓能自然生化;我喜歡清靜虛靈,但百姓能自然按正道而行;我不有意去做事,但百姓能自然富裕起來,我沒有個人慾望,但百姓能自然保持其質樸的本性。
老子·第五十八章——其政悶悶,其民淳淳。其政察察,其民缺缺。禍兮福之所倚,福兮禍之所伏。孰知其極?正復為奇,善復為妖。人之迷,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,廉而不劌,直而不肆,光而不耀。
分析:天下的政治好像不清楚,但是百姓能風俗淳樸;天下的政治好像明明白白,但是百姓卻有太多的缺憾和疏懶。災禍是福氣產生的根源,福氣是災禍藏伏的處所。這樣禍福相互交替,有誰知道何時是極限呢?天子沒有按正道去做,天下走正道的人也會變為追求奇變的人,善良的人也能變為妖孽。人們處在迷惑之中,時間本來就已經很久了。因此,聖人保持自我的方正,卻不按唯一的標準去要求眾人;保持自我的清廉寡慾,卻不割裂傷害眾人;保持自我的率直,卻不隨意做事;保持自我的明察,卻不炫耀自我。
老子·第五十九章——治人事天,莫若嗇。夫為嗇,是謂早服;早服謂之重積德;重積德則無不克;無不克則莫知其極;莫知其極,可以有國;有國之母,可以長久;是謂深根固柢,長生久視之道。
分析:君王治理百姓、運用天道,沒有比節制收斂更好的。所謂機制收斂,這就是說要早些按天道做事。早按天道做事,就是要不斷積蓄道德;不斷積蓄道德,就無所不勝;無所不勝,就沒有人知曉道德的極限;沒人知曉道德的極限,就可以擁有國家社稷。能夠擁有了治理國家的根本道理–大道,就可以使國家更加長久,這叫做根深蒂固,是保持生命長久、保持明察的總原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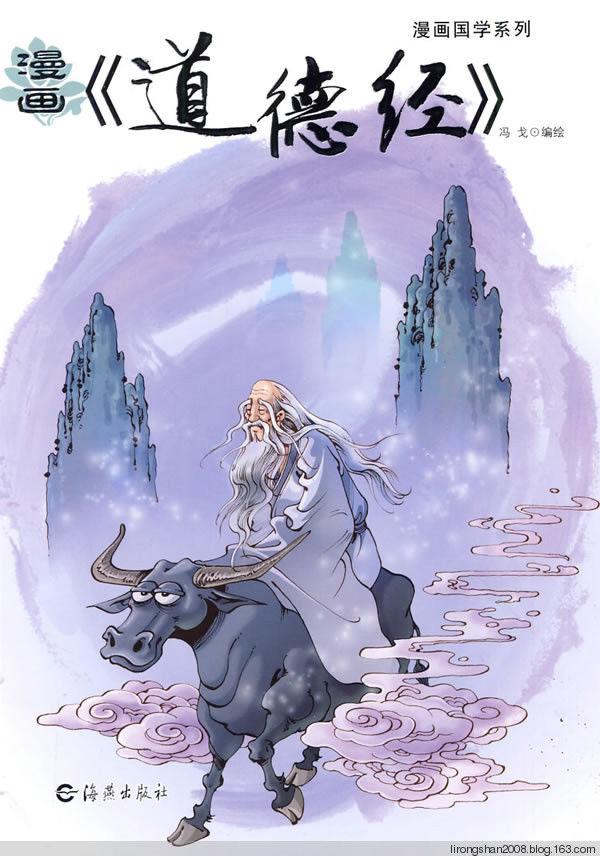
老子·第六十章——治大國,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,其鬼不神;非其鬼不神,其神不傷人;非其神不傷人,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,故德交歸焉。
分析:治理大國,卻像烹制小魚一樣,不須去腸去鱗等加工,只要直接烹制就可以了。這就是說要用無為的大道來作為治國的方法。根據大道來管理天下大事,鬼神也安於其所在,而不出來擾亂人世。其實不是鬼神不出來擾亂,而是即使出來也不傷人。不是鬼神出來之後不傷人,而是聖人在治理天下的時候也從不傷害人。神鬼和聖人都不相互傷害,所以,道德也就在聖人這裡得到了結合與歸宿。
老子·第六十一章——大國者若下流,天下之交,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,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,則取小國。小國以下大國,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,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蓄人,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所欲,大者宜為下。
分析:大國應當自己自願處在小國的下面,使自己成為天下士民的交會之地,成為天下人的陰柔寧靜的立身之處。陰性永遠要用寧靜來戰勝陽性,也就是要把寧靜表現為謙虛卑下。所以,大國用卑下謙虛的態度對待小國,那麼,就能得到小國真正的擁護。小國能夠用卑下謙虛的態度對待大國,那麼,就能得到大國的信任。也就是說,國家不分大小,都應當以謙虛卑下自處。因此,或者表現為大國通過謙虛來得到小國的擁護,或者表現為小國通過謙虛來得到大國的信任。 大國不過是想要兼容並蓄更多的人,小國不過是想要進入大國之中來做事。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,都能各自得到他們所想要的結果,這是很自然的事,但是,大國應該永遠保持謙虛卑下的態度,而不能恃強大而自傲。
老子·第六十二章——道者萬物之奧[1]。善人之寶,不善人之所保[2]。美言可以市尊,美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,何棄之有?故立天子,置三公,雖有拱璧以先駟馬,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?不曰:求以得,有罪以免邪?故為天下貴。
注釋:[1]「奧」字,河上公注為「藏」,王弼注為「庇蔭」,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甲、乙本均作「注」,讀作「主」。其實,道作為萬物之「主」,已將「保藏、庇蔭」萬物的意思涵括進去了。[2]「保」字,任繼愈和陳鼓應的譯文,均依河上公「道者,不善人之所寶倚也」,說「道也是惡人所要處處保持的」。
翻譯:道是萬物的主宰,善人的寶貝,罪人的中保。美好的言詞固然可以博取尊榮,美好的行為固然使人得到敬重,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棄絕呢?所以,就是立為天子,封為三公(太師、太傅、太保),財寶無數,榮華加身,還不如坐進這大道里呢!古時候為什麼重視道呢?不就是因為在他裏面,尋求就能得着,有罪能得赦免嗎?所以道是天下最尊貴的啊!
老子·第六十三章——為無為,事無事,味無味。大小多少,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,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,必作於易,天下大事,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,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,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,故終無難矣。
翻譯:把清靜無為當成作為,以平安無事作為事情,用恬淡無味當作味道。以小為大,以少為多,以德報怨。在容易之時謀求難事,在細微之處成就大事。天下的難事,必從容易時做起;天下的大事,必從細微處着手。所以,聖人自始至終不自以為大,而能成就其偉大的事業。輕易的許諾,必不大可信;看起來容易的,到頭來必難。所以,聖人猶有艱難之心,但終無難成之事。
老子·第六十四章——其安易持,其未兆易謀。其脆易泮,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,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,生於毫末;九層之台,起於累土;千里之行,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,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,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,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,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慾不欲,不貴難得之貨;學不學,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,而不敢為。
翻譯:安然平穩,便容易持守;未見兆端,可從容圖謀。脆弱不支的,容易瓦解;細微不顯時,容易消散。要趁事情未發生時努力,要趁世道未混亂時治理。合抱的粗木,是從細如針毫時長起來的;九層的高台,是一筐土一筐土築起來的;千里的行程,是一步又一步邁出來的。人為努力的,必然失敗;人為持守的,必然喪失。所以,聖人不是靠自己的作為,就不失敗;不是自己努力去持守,就不喪失。 世人行事,往往是幾近成功的時候又失敗了。到最後一刻還像剛開始時一樣謹慎,就不會有失敗的事了。所以,聖人要世人所遺棄不要的,而不看重世人所珍惜看重的;聖人學世人以為愚拙而不學的,將眾人從過犯中領回來。聖人這樣做,是順應萬物的自在本相,而不是一己的作為。
老子·第六十五章——古之善為道者,非以明民,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,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,國之賊;不以智治國,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稽式。常知稽式,是謂「玄德」。「玄德」深矣,遠矣,與物反矣,然後乃至大順。
翻譯:古時善於行道的人,不是使世人越來越聰明,而是使世人越來越愚朴。世人所以難管理,就因為人的智慧詭詐多端。所以若以人的智慧治理國家,必然禍國殃民;若不以人的智慧治理國家,則是國家的福氣。要知道,這兩條是不變的法則。能永遠記住這個法則,就叫至高無上的恩德。這至高無上的恩德啊!多麼奧妙,多麼深遠,與一般事理多麼不協調,甚至大相徑庭,然而,唯此才是通向大順的啊!
老子·第六十六章——江海之所以能為百穀王者,以其善下之,故能為百穀王。是以聖人慾上民,必以言下之;欲先民,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,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,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翻譯:大江大海能匯聚容納百川流水,是因為它所處低下,便為百川之王。若有人想在萬民之上,先得自謙為下;要為萬民之先,先得自卑為後。聖人正是這樣,他在上,人民沒有重擔;他在前,人民不會受害。所以普天下都熱心擁戴而不厭倦。他不爭不競,謙卑虛己,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相爭。
老子·第六十六章——江海之所以能為百穀王者,以其善下之,故能為百穀王。是以聖人慾上民,必以言下之;欲先民,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,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,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翻譯:大江大海能匯聚容納百川流水,是因為它所處低下,便為百川之王。若有人想在萬民之上,先得自謙為下;要為萬民之先,先得自卑為後。聖人正是這樣,他在上,人民沒有重擔;他在前,人民不會受害。所以普天下都熱心擁戴而不厭倦。他不爭不競,謙卑虛己,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相爭。
老子·第六十七章——天下皆謂我道大,似不肖。夫唯大,故似不肖。若肖,久矣其細也夫!我有三寶,持而保之。一曰慈,二曰儉,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;儉故能廣;不敢為天下先,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;舍儉且廣;舍後且先;死矣!夫慈以戰則勝,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,以慈衛之。
翻譯:世人都說我的道太大,簡直難以想像為何物。正因為他大,才不具體像什麼。若具體像什麼,他早就藐小了。我有三件寶貝,持守不渝。一是慈愛,二是儉樸,三是不敢在這世上爭強好勝,為人之先。慈愛才能勇敢,儉樸才能擴增,不與人爭強好勝,才能為人師長。 當今之人,失了慈愛只剩下勇敢,失了儉樸只追求擴增,失了謙卑只顧去搶先,離死亡不遠了!慈愛,用它來征戰就勝利,用它來退守必堅固。上天要拯救的,必以慈愛來護衛保守。
老子·第六十八章——善為士者,不武;善戰者,不怒;善勝敵者,不與;善用人者,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,是謂用人之力,是謂配天古之極。
翻譯:真正的勇士不會殺氣騰騰,善於打仗的人不用氣勢洶洶,神機妙算者不必與敵交鋒,善於用人者甘居於人之下。這就叫不爭不競之美德,這就是得人用人之能力,這就算相配相合於天道。上古之時便如此啊!
老子·第六十九章——用兵有言:「吾不敢為主,而為客;不敢進寸,而退尺。」是謂行無行;攘無臂;扔無敵;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,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若,哀者勝矣。
翻譯:用兵者有言:「我不敢主動地舉兵伐人,而只是被動地起兵自衛;我不敢冒犯人家一寸,而寧肯自己退避一尺。」這樣,就不用列隊,不必赤臂,不需武器,因為天下沒 有敵人了。最大的禍害是輕敵,輕敵幾乎能斷送我的寶貝。所以若兩軍對峙,旗鼓相當,那悲傷哀慟的一方必勝無疑。
老子·第七十章——吾言甚易知,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,莫能行。 言有宗,事有君。夫唯無知,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,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。
翻譯:我的話很容易明白,很容易實行。天下的人卻不能明白,不能實行。(我的)話有根源,(我的)事有主人。你們自以為有知識,所以不認識我(的話和我的事)。明白我的人越是稀少,表明我所有的越是珍貴。所以聖人外表是粗麻衣,內里有真寶貝。
老子·第七十一章——知不知,尚矣;不知知,病也。聖人不病,以其病病。夫唯病病,是以不病。
翻譯:知道自己無知,最好。無知卻自以為知道,有病。只有把病當成病來看,才會不病。聖人不病,就是因為他知道這是病,所以不病。
老子·第七十二章——民不畏威,則大威至。無狎其所居,無厭其所生。夫唯不厭,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;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
翻譯:當人民不再敬畏任何人的權威時,真正的大權威就來到了。 不要妨害人們的安居,不要攪擾人們的生活。只要不令人們生厭,人們就不會厭惡權威。所以,聖人深知自己,卻不自我炫耀;他珍愛自己,卻不自我尊貴。
老子·第七十三章——勇於敢則殺,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,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,孰知其故?天之道,不爭而善勝,不言而善應,不召而自來,繟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,疏而不失。
翻譯:有勇氣自恃果敢,冒然行事的,必死。有勇氣自認怯懦,不敢妄為的,得活。這兩種勇氣,一個有利,一個有害。上天所厭惡的,誰曉得個中原委呢?上天的道,總是在不爭不競中得勝有餘,在無言無語中應答自如,在不期然時而至,在悠悠然中成全。上天的道,如同浩瀚飄渺的大網,稀疏得似乎看不見,卻沒有什麼可以漏網逃脫。
老子·第七十四章——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懼之?若使民常畏死,而為奇者,吾得執而殺之,孰敢?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殺,是謂代大匠斲,夫代大匠斲者,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翻譯:人民若不怕死,以死來恫嚇他們又有什麼用呢?如果先使人民懼怕死亡,有為非作歹的人再處死,這樣誰還敢為非作歹呢? 冥冥永恆中,已有一位主宰生殺予奪的。企圖取而代之去主宰生殺予奪的人,就好象外行人代替木匠砍削木頭。代替木匠砍削木頭的人,少有不傷著自己手的。
老子·第七十五章——民之飢,以其上食稅之多,是以飢。民之難治,以其上之有為,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,以其上求生之厚,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,是賢於貴生。
翻譯:人民吃不飽,是因為統治者吃稅太多,所以吃不飽。人民不好管,是因為統治者人為造事,所以不好管。人民不在乎死,是以為他們追求今生太過份,以致不在乎死。所以,唯有不執著於今生享樂的,比那些過份看重今生的人更高明。
老子·第七十六章——人之生也柔弱,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,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滅,木強則折。強大處下,柔弱處上。
翻譯:人活着的時候,身體是柔弱的,一死就僵硬了。草木活着得時候,枝葉是柔脆的,一死就枯槁了。所以堅強的,屬於死亡;柔弱的,屬於生命。草木之生也柔脆,其死也枯槁。軍隊一強大就要被消滅了,樹木一強盛就要被砍伐了。強大的處於下勢,柔弱的處於上勢。
老子·第七十七章——天之道,其猶張弓歟?高者抑之,下者舉之;有餘者損之,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,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,則不然,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?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,功成而不處,其不欲見賢。
翻譯:上天的道,不就像張弓射箭一樣嗎?高了向下壓,低了向上舉,拉過了松一松,不足時拉一拉。上天的道,是減少有餘的,補給不足的。人間的道卻不這樣,是損害不足的,加給有餘的。誰能自己有餘而用來奉獻給天下呢?唯獨有道的人。所以,聖人做事不仗恃自己的能力,事成了也不視為自己的功勞,不讓人稱讚自己有才能。
老子·第七十八章——天下莫柔弱於水,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,以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,柔之勝剛,天下莫不知,莫能行。是以聖人云:「受國之垢,是謂社稷主;受國不祥,是為天下王[1]。」正言若反。
注釋:[1]國之污垢,即罪惡;擔其罪,即受辱。不祥,即凶殃;承其凶,即受難。
翻譯:天下萬物中,沒有什麼比水更柔弱了。然而對付堅強的東西,沒有什麼能勝過水了。這是因為水柔弱得沒有什麼能改變它。這個柔弱勝剛強的道理,天下的人沒有不知道的,卻沒有能實行的。所以聖人說:那為國受辱的,就是社稷之主;那為國受難的,就是天下之王。這些正面肯定的話,聽起來好像反話一樣,不容易理解。
老子·第七十九章——和大怨,必有餘怨;報怨以德,安可以為善?是以聖人執左契,而不責於人。有德司契,無德司徹[1]。天道無親,常與善人。
注釋:[1]古時借債,刻在一塊板上,劈開,債主存左邊,債人存右邊;此為「司契」。「司徹」則是貴族按成徵收稅租。
翻譯:用調和的辦法化解怨恨,怨恨並不能消失貽盡,這豈算得上良善呢?所以,聖人掌握著欠債的存根,卻不索取償還。有德之人明潦欠債而已,並不追討;無德之人卻是苛取搜刮,珠鎦必較。上天之道,公義無私,永遠與良善的人同在。
老子·第八十章——小國寡民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;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,無所乘之,雖有甲兵,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樂其俗。鄰國相望,雞犬之聲相聞,民至老死,不相往來。
翻譯:國家小,人口少。即使有十倍百倍於人力的器具也不使用。人們畏懼死亡而不遠行遷徙。雖有車船,卻沒有地方使用;雖有軍隊,也沒有地方部署。讓人們再用結繩記事的辦法,以其飲食為甘甜,以其服飾為美好,以其居處為安逸,以其 習俗為快樂。鄰國的人們相互可以看見,雞鳴狗叫聲相互可以聽到,但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互往來。
老子·第八十一章——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,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,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,既以為人己愈有,既以與人己愈多。天之道,利而不害;聖人之道,為而不爭。
翻譯:可信的不華美,華美的不可信。良善的不巧辯,巧辯的不良善。真懂的不廣博,廣博的不真懂。聖人不為自己積攢什麼:既然一切都是為了世人,自己就愈發擁有了;既然一切都已給了世人,自己就愈發豐富了。上天的道,有利於天下,而不加害於天下。聖人的道,是為了世人,而不與世人相爭。
 明天機周易網
明天機周易網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